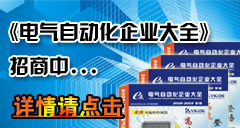理論一:國學式管理
|
| (發布日期:2007-12-30 10:57:56) 來源:《牛津管理評論》 |
![]() |
| |
兩個現象引起的思考
一個現象是:“國學熱”可謂持續升溫,從有大學開辦國學院、國學講座,到接連出現的國學短信、少兒讀經班、“孟母堂”及國學博客圈,以及漢服熱、成人禮的興起;放大到國際背景,從全球聯合祭孔,到孔子學院在不少國家紛紛建立,以及漢語熱在世界范圍的升溫等等,尤其是以于丹和易中天為代表的國學熱,成為2006年以來中國文化界的特大現象,《于丹《論語》心得》和《易中天品三國》。
另一個現象是:以曾仕強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式管理”自去年起也成為中國企業管理界的熱門話題,曾氏旋風不亞于前幾年的“杰克 韋爾奇熱”。這種思維最近幾年很流行,以至于中國的四大古典文學名著都被中國的企業家當管理書籍來讀了。“水煮三國”、“孫悟空是一個好員工”、“王熙鳳是一個好領導”,《水滸傳》就不用說了,簡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管理教材,這種思維方式都是“中國式管理”。
于丹們、易中天們和曾仕強們早已不是一般的學者和專家,而是明星,是一種現象,兩者之間是否有必然聯系?而清華等大學開設的“國學總裁班”的宣傳更是引人關注,如何看待國學熱與中國式管理的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更多的是盲從和幼稚,有必要對此作出深入的分析。
為此,記者采訪了上海本原企業咨詢研究所所長沈玉龍教授,就此發表了他的看法。
國學熱:形式大于內容精神尋根
時下的國學熱,我們認為首先看成是經濟社會發展后的必然出現的精神尋根。
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經濟高于一切的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演變在實際的過程中,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唯經濟”社會,物質利益的力量彰顯為社會生活中最大的力量和標準。
這是中國社會之大幸,也是不幸。說是大幸,是因為這是對政治社會的糾正;說是不幸,是對人性和社會的片面糾正。
學理上的合理,大多是建立假設和時候諸葛亮式的評價上,社會的發展并不是實驗室的實驗,是在絕對的空間和約束條件下進行的,因此,當有人對前二十多年物質高于精神的畸形現象憤懣不平時,實際上最多是一種理性的假設理想吶喊,學理上合理但事實上難于做到。
事物的發展總是這樣,物質缺少時追求物質,物質豐富時追求精神,這是辨證的和合理的。
當前出現的國學熱,正是中國社會經濟得到充分發展時提出的課題。
在沈玉龍教授看來,國學熱表證的與其是社會這個大寫的人的精神缺失,不如更多的是小寫的人的精神空虛,因此熱背后是精神尋根。
二十多年中國社會事實上的精神缺失、信仰危機、精神焦慮和心理失衡,成為經濟發展過程中潛在的最大危險。為什么要追求物質和財富,除了滿足人們生活的享受外,物質和財富對于我們究竟還有什么意義?物質和財富的追求到底有沒有邊界?這些問題的困惑,使得人們對物質以外要素的思考成為必然,而這一切只有在物質追求得到基本滿足后才能提出,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否則空談精神是沒有意義的。
文革帶來的中國文化斷根,使得中國人不知傳統文化為何物,一個沒有民族文化修養的中國人,很難算是一個合格的中國人,全球化時代不僅需要的是世界文化和融合,更需要民族文化的張揚和發揮。
很難想象一個民族可以沒有文化,也很難想象一個企業可以沒有文化。當中國企業進入到世界競爭環境中時,我們發現缺少的恰恰是精神氣質。
當源自于西方社會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經濟領域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時候,當西方的管理技巧被人們在商場上無所不用其極的時候,人們終于發現,一切社會的弊端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還出于我們的自身,出自“德”的缺失,許多人不僅忽視了自己做人的價值,也沒有看到旁人的價值,結果引起社會不和諧。
國學本來就是中國的精神財富,而在中國崛起之際,對抽象的精神的追求也是必然之途,這正好是國學復興的機遇。
1913年,英國人莊士敦曾經這樣說過:“當我們歐洲人開始驚異地發現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中國的道德倫理、中國的藝術和文學都有崇高價值的時候,中國人自己卻開始學著把他們文化中這些偉大的產物加以不耐煩的鄙視……,這是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現象。”
今天,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文化本身具有的精神價值及其這種精神價值對我們的意義時,國學開始成為熱也不足為奇了。
而我們眼下最為關注的不是國學該不該熱,而是國學該怎樣熱的問題。
必須冷靜地看到,時下有三種不恰當的現象:
一是:忘卻歷史不負責任地一講國學就什么都是好的,甚至有國學復古的狀態。作為一種文化價值系統,“國學”早已被歷史的決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運;但從人文價值系統的重構來看,“國學”又不無“花落春猶在”的意味。中國近代以來文化變革的歷史,就是西方現代文明與中國封建文化之間抗爭的歷史,目前國學熱中有一種復古傾向,值得警惕。許多專家一談國學,就什么都是好的,無論是儒家的學說還是道家的觀點,一概都是對的,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是對人們的誤導,值得警惕
二是神秘化的傾向。翻開大量的書籍,我們發現有對國學神秘化的現象,最為典型的是對《易經》和道家學說進行神秘化,使國學走上封建迷信的老路,這幾年風水的流行、年輕人對算命的熱衷等現象,就是國學神秘化的體現。
三是注重皮毛重于內容,形似神不似。許多書籍和專家抓住一句話大做文章,斷章取義,夸大其詞,其實是一種低水平的說法,嚴重誤導了民眾,甚至有所謂的專家,連一本古代經典著作都沒看過,就大談所謂國學和管理。
中國式管理:是人學還是科學
中國商人“言必稱德魯克”到“言必稱國學”的轉化之快有時也讓人瞠目結舌。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與實踐,走的是實踐在前理論在后的路子,然而企業的發展光是摸著石子過河總是危險的。
因此,二十多年來中國企業對管理理論的渴望和追求,成為一個社會現象。而中國本身的計劃經濟理論是無法滿足企業的需求,為此,MBA熱成為一個奇特的中國現象。
在MBA熱背后,確實讓中國的企業家和經理人學到了系統的經營管理知識,但是也存在非理性和浮噪的普遍現象。
“言必稱德魯克”就表明許多企業并不遵循“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原理,以為西方的管理是靈丹妙藥,結果給自身帶來沉重的打擊。
有企業家認為:“MBA、企業管理等東西我都學過,但是我覺得這些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的問題。我系統學習過中西方哲學,這些中國的傳統思想、觀念給了我很大啟發。為什么我們在生意上會遇到很多問題,我覺得還是對對方不了解,歸根結底是對中國文化背景不了解。學國學確實能從思想上解決企業的問題。”
海南航空集團董事長陳峰陳師從南懷瑾,平日里喜著中式對襟衫、練功褲、布鞋,一身素白,仿若太極打扮,愛圍棋、談儒禮佛,新晉商陳峰的另類面孔總是引人注目。在海航內部,陳峰要求員工必備兩冊書:一冊《中國傳統文化導讀》,一冊以南氏精髓編寫的《員工守則》。守則開宗明義:“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今年7月,為慶祝班機直航比利時,海航在布魯塞爾開會。結果陳峰與中方管理層一色的雙襟扣大褂,吸引了不少目光。
國內商界中,“陳峰們”人數并不眾多,但有跡象顯示,這個“隊伍”正在逐步壯大。
痛定思痛,中國古典智慧卻給了管理界一個全新的視野空間:易經、孔孟思想、老子思想、孫子兵法……“中國式管理”應運而生。
沈玉龍教授認為曾仕強的概括基本上可以說是對“中國式管理”的比較全面概括。曾仕強認為,“中國式管理很簡單,就是你先把人做好,然后才能談管理。”他認為,中國式管理的三大主軸是“以人為主、因道結合、依理而變”。這三者的關鍵都是人,它們主張有人才有事,事在人為,以理念來結合志同道合的人,合理地解決問題,而不是凡事“依法辦理”。安人先修己,美國式管理強調“我要—我成”,訂立目標,拿出成果;日本式管理則重視“同生—共榮”,合力追求團體的榮譽,不計較個人的榮辱;而中國式管理卻是“修己—安人”,以“怎么樣都好”的心情,以自然的方式自得其樂地順勢行事。
崇尚彈性管理是中國式管理的第二個主要觀念。與西方的組織相比,中國人的組織大都是“很實際地寓人治于法治”,人治的色彩更濃厚一些,而人治往往會帶來彈性管理。曾仕強認為中國式管理的彈性是由于不確定性和內外部環境的快速變化而產生的。
中國式管理貢獻的第三個主要管理觀念是“中庸”合理。他認為中庸之道應正名為“合理主義”,這樣它的真正用意才更清晰。
|
版權聲明:
凡本網注明來源為“中國電氣自動化網”的,版權均屬于中國電氣自動化網,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電氣自動化網”。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本網轉載自其它媒體的信息,不代表本網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轉載均有出處,本網對轉載文章不存在侵權等法問題。 |
|
|
|
|
|